
夜深沉 90×150 板上油彩 牛放 2019
第二回
非弓非弩驱除鞑虏
非亲非故黄土一抔
来上岗时,跟小高聊了一路的王小波,她喜欢他写的情书,不喜欢他的小说。
“王二太二妄。”
“他那是叫唤出来的诗,跟崔健吼出来的歌一样。”
“啊――那句:‘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我笑着摇头的时候,老占对着挡风玻璃,卯足了劲儿大声说:“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我和小高都瞪大了眼,对视了一下,看向他。车正对着阳光,老占的粗脖子通红。“俺媳妇老家是青虎山的,她教我的。” “有文化!”“挺细腻!”的评语使他借着车的颠簸,丢荡着单挂在耳朵上的口罩,像只大公鸡。
“四十多岁就死了,真可惜。”
“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他的魂儿。”
窗外,车灯里,开发区的界牌一晃而过。我父亲的墓就在这向北走的大道边上,以前是老远就能看见的一片东南向的山坳,现在被好多个4S店遮住了。清明节陵园封闭,过了一个星期,去管理处买纸和香,大厅里新立了个照壁,中英文对照:“一花一世界,一砂一天堂,掌盛无边触,刹那即永劫。――〔英〕威廉.布莱克”。没写谁翻译的。词语对真理的驱动不分东、西,字词的翻译也有灵魂的力量。查了后,猜是将宗白华先生的翻译改了,为了贴合公墓的氛围。老先生是旧学的里子,新学的面子,底气是儒释道,续了往圣的绝学。
我父亲那辈人生于战乱长在动荡,赶上了国家的昂扬向上,吃过苦遭过罪却大都无怨无悔。因为是学工科的,不讲究至理,主要追求致用,在场面上说话,不会左也不会右,只适应事,道理、德行点到为止。中年时读些苏俄文学、古典名著,到了晚年买了各种国学读物。很少说忠心耿耿、海誓山盟之类的话,觉得掉价。有一年,他退休后顾问过的一个大佬涉黑,来调查的警察要帮着提菜上楼一趟,他说好。进门拿了手机,告诉我妈让我回家等着去接他,就跟着走了。没想到时间全用在了路上,挺远的。大半夜,第二拨询问的警察说:“没你什么事了。要不在招待所住下?报销。”他说不用,拿回手机,打了电话,在门厅里等到天大亮。七年前,开发区医院的内一病房,他去世前一天的早晨,说起那件事,我问他:“反正没事了,大晚上的,着什么急?”他保持着医生要求的仰卧和平静,说怕我妈害怕。“那帮警察不如意大利的。八几年来着?登记可仔细了,十字、卍字、法西斯、咱的党徽,意餐、法餐、就没中餐,都得打X打勾。诶,对了,等会儿豆腐脑里多放点韭花。嘴里没味儿。没事儿,我知道。”摸了一把白胡子茬,摁摁胸口上的电极片,等着剃须刀充好电自己刮。他们的时代让他近乎无欲无求,除了名誉和亲情。
王小波比他们晚一辈,算是老三届的尾。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漫卷的天下,拨乱反正、春潮涌动、东渐入海都赶上了。“东风吹,战鼓擂,干革命,谁怕谁?想当初,他上青虎山东李家疃,算是插队。”作协主席把洗茶的开水浇在黑蛤蟆上,闻了闻黄蛤蟆,说起从前。“大个儿干干劲儿,没几遭就歇菜了,板儿不行。当老师挺能白白,可一开会儿就发梗。队长摆辈他应该叫舅,好一个照顾。留个长毛儿,没事儿就拿根棍儿,上山下乡穷逛荡,说是美。生产队的驴都让他骑遍了,腿长没摔着。前塂后夼的狗见了都不咬,说是个狗圣。越传越邪乎,还会算命!”综合他学了那么多专业,会干那么多活儿,传言应该不虚。但是,他杂文里的泼辣与深刻在那时就暴露了端倪?他小说里的那些凄美与挣扎,是来自地瓜干对胃的折磨,还是天南地北的水土不服?那些粗俗却隽永的诗句,是来自山清水秀的乡间,还是街坊邻居间的口头语?有机会聊聊,没什么意义,但挺有趣。北风那个吹,雪花儿那个飘,不高的塂,不大的夼,魂牵,梦绕。
零点用手机的时候,看到小鱼儿传了半截儿的“盛世美颜”,可能是转传的电脑原图,太大,噎住了。再看时,又发了几张手机拍的照片,有酒吧,有茶室,还有咖啡座,留言问哪个漂亮?我回复“没传完得漂亮。”让她不睡觉!我猜,她想用修整好的剪影影响一下我,别把她画成了“弗朗西斯的培根”,只不过太较真,断送了。那几张室内的景,可能是给我提供点谈资,帮金总解析一下小乔的方案。准备塞回手机,语音短信来了。“我准备接手三楼,”语速很慢,但睡意不多,“已经让小乔跟他妈商量了,做那种沉浸式展示的画廊。到上海来取取经,准备去深圳踩踩点儿。”想回个惊讶的小图标,想起她总是有点滞后的表情,又觉得点赞也行。“刚回来,睡会儿,回去再找老师聊。”回了个OK,“肖像确实还得改,我把她画得太文静了。”
下了立交桥,从高铁下穿过,上了环山路。向北望,密密匝匝的楼群,下弦月状的海湾,晨雾里,没睡醒。
这座城市英文名是Chefoo,延用了秦始皇对它的称谓,近代以峰燧得名的海港命名,因为被迫开埠和一个不平等条约出名,因为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的锅炉房始终是戍守的食堂,而籍籍无名于两次中日战争。战争不是兵棋推演,外交不是推倒码起的麻将,赢得运气,输了晦气,拍胸脯和拍屁股一样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即使曾文正、左文襄披坚执锐也是纸糊的海防,殚精竭虑的中兴也只能是洋梦一场。立在菜市口的谭嗣同,坐在鱼藻轩的王国维,当时怎么想?
高冠天问,国殇拂袖。
凌波微步,魚山八斗。
鹤背箫声,拾履留候。
广陵曲散,颈断血稠。
我希望什么?我有什么?我能干什么?
我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人民相亲相爱有密有疏,相互竞争有限度没裂度。资本剥削得别太狠,老百姓挣钱挺轻松。春种、秋收顺应天时,南稻、北麦善待地利,你你我我的幸福指数正态分布。国家政治清明法治严肃,士农工商、东南西北不分彼此、戮力同心抵御外侮、抗灾防疫,均衡文明积淀与文化时尚的比重。
希望国际间坐坐、转转、聊聊、谈谈,没有一己一家一族一国一域之私欲无节制的张扬,都排斥处心积虑丧心病狂的舆论场,都拒绝成为别人家的斗兽场,共同规划出一块埋葬罪大恶极的垃圾场。不能,公理的天平一头是你的道理,一头是我的德行。不能,唯我马首是瞻,分不清黑道白道,只认得自己的道。是的,历史上,国际、民族、宗教、利益集团大都奉行霸道,破坏秩序、建立秩序、维持秩序的人都有所谓道统傍身,柏拉图理想国里的正义之王从未出现。也就是说,乐观地看,人的本性里还存有悲天悯人的善念,我们的世界观里仍存有真理的公田,你我他仍保守着对圣贤大德的期盼。但是,人没有欲望就没有我的产生与存在,我在现实中的存在实质是欲念与理念的对立,欲念与理念的均衡态是情感,情感的条理化是心理,心理的规范化是道德,道德的神圣化是信仰,造成情绪的欲念与理念无时无刻不在互动,承现一个活的我。彼此的道德观念可能大同小异,但控制情感解释道德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所谓“只在一念之间”。人要完整地认清自我,就必须有一个我之外的我,那个“祂”――个业与共业赋予我的灵魂。所以,强调互通有无、共生共荣的国际法则,强调保障民生、启发民智、珍视生死的文明共识,覆盖在“物竞天择”的天条之上,纵横捭阖的策略、如履薄冰的戒律充斥着各自的怨与愿――颠覆不破的在劫难逃。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创造历史的人,不怕弄脏自己的手。”他也这么悲观。
我,想用生命赋予我的灵魂把握生命始终之外的存在感,奇怪,乐此不疲,有趣。
车从空阔通亮的遂道穿出,钻进一团山间的雾气。下坡,往南,就会右捌上一段海湾的东岸。天气预报日出在5点10分,晴,“早着呢。”
小于将悠游于亚得里亚海的小鱼儿放回到了家乡这一小湾水里,将自己的审美观打包推送,企图吻合中西合璧的市场指向,温度、湿度、气压都适度。不用顾及安保,因为有娘家,因为有高大上的小乔。饿不着,流域里那个饵料卖的好就投点,钓上个把条海鲫、沙丁,营养也就够了。想吃饱,瞅准一片海,沉下一批虾仔参苗,呼应着上下游,小乔在旁边帮衬着怎么弄都好。想走高端,难,因为心要狠、手要准,别人的话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别人的钱用起来手软,再好的祝愿也拼不过“杠杆”。大家闺秀是大门不出的,横刀立马的是巾帼英雄。小家碧玉可不行,厅堂里迎来送往,厨房里可都是煎炒烹炸,身上的味儿太混杂。“都说闻香识美人,看她手里的花儿,就知道他想干嘛。”视频里,小鱼儿嗅了一下喇叭花,模仿了两下洛可可画中骑士与贵妇的表情,点赞送花的蜂拥。
我那次偶尔地点赞,是在画室里跟她聊天的时候。当时一闪念,社交网络里的我,其实是我的或者,他不死不活,要么死,要么活,都依赖观察者。在画廊这件事情上,我在别人眼里也是那个或者,一个没必要完整的我。现在,我解析我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用时间圈定一个个或者,对于我持续地存在无意义,无聊,我还是我,有趣。明明知道金总是在爬小乔竖的标杆,假装失手就会出溜回原地,还在帮着戳弄,是想找个明显的地方挂上自己的画?八字没有一撇的情况下,就拉学会进驻,是想以后学会有好事别把我忘了?小鱼儿嫁衣还没穿,就扯起婆婆的大旗招兵买马,我高兴什么?因为她有留学的背景,审美观有所雷同?不是。是想不用再随声附和所谓的雅俗共赏,把画摆那就行,即使再搬回来,不是有那句“再聊”嘛。我不指望于经理能代理我的画,好像我们都还没有那样的资质,代售就行。现阶段,我唯一可能善终的就是我的画,当然,它最好包括在我的生命里。我没有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决绝,因为我不信仰什么,只想摸着石头过河,水太深或太冷就换个地方,前提是不包括我的画。我想用画背后的审美观对这个人文环境有所企图,感动就流泪,后悔就唾弃,表面上不越现时的公理共识雷池半步,暗地里扒拉道与德的陈年旧帐。不弘扬,因为有扬就有抑,哪来得活泼。不斥责,因为只要是红嘴白牙的褒贬就是一把双刃剑,舌头太软。我的画笔不适合扫黛点绛,也就涂涂抹抹还行,就像崔老师说的:“大师们定下的调调,咱跟着唱唱。”人家乔托天生就是放羊的命,米开朗基罗是吃着石匠的奶长大的,他们的艺术里本来就蕴含着神性,所以能“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很晚才看到王小波的小说,是在作协创刊号上的《战福》。看到人死成了一条狗,落泪的同时恨作者:“怎么能这么狠?撕掉胸口上刚结的痂。”同时替作协担心:“这杂志能办多久?”结果是,去网上看了王小波大部分的小说,用油彩使劲鞭挞他那张笑得很灿烂但有些苦相的丑脸,就像被他的王二附体;前些日子把“有头有脸”发给作协,说是太长要减一半、其他稿件已经组好、杂志已经很薄。
为什么,各民族都将现代称之为艺术的那个东西作为自我认同的图腾,将当代称之为艺术家的人放在国家、族群文明的祭坛中心?因为人都希望有灵魂,因为灵魂是“我”的存在根本,因为艺术家是灵魂的现成品。文化观念将神性赋予艺术,神性在艺术的加持下奴役文化,艺术在文化反噬神性中被一次次打回原形。艺术是人性探索神性的文化印记,是完整人性或健全灵魂的一种尝试,仅此而已。也因此而长存,物我两忘,地老天荒。然后传奇,然后演义,然后考据,然后……
东山博弈,谢客制屐。
骠骑柱国,右军流觞。
寄奴北望代兴时,东西拓跋启隋唐。
曹衣出水,阿弥陀佛,
吴带当风,菩提萨垛。
媚娘狐媚,牝鸡司晨。
太真天真,马嵬成尘。
一江春水亡国恨,夜宴舟中有贤臣。
云在青天水在瓶,溪山行旅踏歌行。
一河两岸君子树,永乐宫里朝三清。
秋风纨扇的唐解元耽搁了治平的前程,
徐文长的明珠落成了八大小鸟的眼晴,
顾炎武骂的不是柳如是的肤白心冷,
石涛的粗头乱服拖泥带水似朱还青。
老莲,髡残,四王,八怪,赢台血泪珍妃井,青埂峰下红楼一梦。
车上了滨海路。晨跑的人戴着口罩,跟着的狗吐着舌头。我开玩笑地问小高,这符合防疫规定?她皱了下小鼻子,笑着说“不到处拉就行。”“现在放风最安全,”老占提醒。问小高医院战疫阶段性胜利的奖金怎么分?
“分三块儿,一是本职,二是抗疫,三是分数。分儿高的在平均数上加70,少就减70。科室总共十个人,正副三个领导一等,剩下两个名额全员投票。问大家有没有意见?都举手了。”
“飙!那俩副的凭么拿一等,真干的多?”
“都想让他俩给咱也投一票。”
“这不是少了70的面子,是丢了一百四的梗心,要争!”
“怎么争?还能不举手?”
“把那俩副的拉下来一起评。”
“你这一反就得罪三个人,绝对是最后一名,白干了!”
“哼!老牛,你们那儿怎么弄的?”
“类似。”
“怎么个类似?”
“打分,简单,女的不出远门、不顶夜班,不就分清了。不过这次是志愿,跟钱没关系。”
“怕是你说的吧。简单麽?小高,这样的小妈,不就吃亏了?”
“小孩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呲,单位都是咱家的。谁吃肉谁喝汤,大xx队长内定了,不屌的走人!”
“那倒简单。”
“简单麽?还得争!这个监控,走错路罚十分,还有超速,一中着儿――白干!这摄像头,抽烟,一分,抗疫,更狠。以前还有打瞌睡,俺这样的眼小,咋办?得争!”
“哈、哈,”小高笑得手捂着肚子,本来翘起的面罩扣回到了脸上,闷声问“瞎谝呢?”
“扣我的!”我赶紧接过话头。
“这鸡儿的独眼,”老占向摄像头伸了一下圆下巴,“管么都能看见。”
“它不歇会儿?”
“不管黑白地照。出了事儿,一回放,一推拉鸡儿倒。”
“哎――是啊,慢点儿吧。”
“我知道。”
微信里叮咚了好几声,是焦馆长的诗被谱成了抗疫的歌――《冲锋号》,时间掐得挺好。“先把接送任务完成了再听,快到喽!”。
步行街的早点摊已经开火,环卫的垃圾车呼啸着向城区外开去。车停稳了,那个海员还没醒,小高过去叫。我到隔离指定酒店的后门交上登记表,签上字,拍照,发到网上。出来时老占在倒车,车大,就帮着看着点儿后面的情况。一个小孩儿拉着老人的手提着早饭看向我,“姥爷,白衣天使!”怔怔地说。我赶紧闪开两步指了指小高,隔着口罩面罩大声说:“那个是真的,我是假装的。”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概念突然有了声音,吓得小孩往老人身上靠。
到了医院,老占想去北市场兜一圈,小高说着“那我就打的吧,”提着要销毁、消毒的装备下了车。我对占师傅说:“都挺不容易的,这大清早的,哪来的出租?送送吧?我走。”
穿出巷子,上了东关路,离家不远了,耳朵已经把抗疫神曲忘了,继续强劲凄美的“小红梅。”
星期六的早晨,大街上人很少。有点冷,想擤一下鼻涕,发现手绢落在了隔离服里。想起前天在金总那儿说道过的尚老师的事。
矫局问:“老尚到底怎么回事?”
金总说:“脑瘤,保守治疗,不让告诉别人。话巳经说不清了,医生说倒记时吧。先开始大刘找人照顾着,现在他老婆在那儿看着。这不放署假吗,中午在这儿,下午去那边学书法,晚上去他小姨那儿。我先垫着,有合作医疗。吃进口的能多活两天?听天由命吧,哎!”
“可能就在这个医院。去不去看看?早,晚?睡一觉再问?去了干什么?绝别?这一瞥是一块石头落地还是落水?不是就当没事,是别找事。都是等着的死活,一把火就了喽!另一个世界,物理都变了,再见什么?那里一定有求必应,不然怎么没个回来的?再说吧。”
容易忘事,最主要原因是旧有习惯,出错先检讨自己,自认为没错就过去,忽略了后续的失语、失速、失去。在儿子填报高考志愿要先挑专业时,我支持说:“宁可低就,不要高攀。”看似赢得了主动,实则妄断现实待遇,需要反省。在四楼小乔那儿,看到他收藏的卡百利唱片和海报,以为找到了个英伦摇滚迷,其实他还捣腾潮玩和盲盒,过过手的兴趣而已。抓住“劫掠”中的德国梅特涅,给他们聊奥匈帝国的梅特涅,没反应,说走也没人留,是没错,却是自己以为的。老年人总爱拿自己的所谓丰富的经验评价别人的说辞,没想到别人只是说说而已,听的是你的态度。画画确实需要经常钻钻牛角尖,像搞学问一样,把观念和造型一一对位,明辨是非才能饱满情绪,才可能冲锋在前。而现实中,文化要求艺术富含娱乐的无止境和审美的局域性,强行用学术去圈地、兑现、整合,应该是愚蠢。
“旗帜”的焦馆也想把美术馆招展出个样子来,假以官办截取体制资源,利用话语权圈养审美,以圈套圈循环放大效益,高攀不起;民间那种开店、赶集、摆摊、抄股式的捣腾,吹拉弹唱的吆喝,生旦净末丑的扮相,又看不上。“现在这样,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展一下,招来的就那么几个文化人,灯底下没几个人影,跟个会所一样。接接地气,办个沙龙画廊吧?这么多喜欢老房子老街的游客,也要有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嘛!这灯塔下的一片港湾,高高矮矮的小洋楼,还是挺有诗意的!先别管雅俗共赏,先把展览密集起来,不怕进不了排行榜。要不你过来?咱给他摆弄出个艺术副刊,我扇风你点火,串连加窜联,就――就――重庆那种串串香,别管生熟,先给它煮上。真材实料,冰凉滚烫,盆儿碗儿碟儿一齐上,红的白的你一盅我一盅,嘿嘿――那滋味!先别想着先验,要实验。占编辑部的编不就得啦。大棚里,有几样不是趴着长的。”我惭愧却没说答应,是因为改编制这事儿不能靠舌头在唾沫里涮出个结果,不能拿还有十年的工龄破釜沉舟。这事可行,但短板是我:一、只干过班主任,管大钱管大人都不行;二、散漫惯了与人打交道呆板;三、干事的方式和画画差不多,避虚就实、避轻就重、摸索直行,绝对和他合不来。他在一个演讲视频中说:“开天眼,其实就是将互联网变成自己的视网膜。用你的法眼透视市场与制造的关联,将形成市场的文化指向转化为创新的指标,先与受众感知未来。使消费合流于文化追求,使商业不再是囤积居奇,使制造成为汇聚市场力量的湍流,识心达本,直入顿超。”掌声里他倍儿直的腰板儿面对的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我面对的是,人在各种场景中或佝偻或挺拔的身姿,或诧异或欣然的那张脸,以及,像植物一样被栽种、像动物一样被放逐的心,即使画风景,空间和时间都是心境,色彩和造型只有在我把它们忘记时,才会自主的凝重、涌动,要有自知之明。我的数学能力也就到一元二次方程,初中?语言能力留级在宋明蒙学句读,够不到八股,够呛!世界观是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加辩证,还行?所以,我希望面对的世界是我能够面对的世界,可以有真理的五花八门的正解与畸意,可以将道德作为匕首或箭矢的正义或歹意,不能容忍的是,将美堕落成伪真、伪善的糖衣――丧尽天良、别有用心。我认为,人在感受美中存在,在审察判断美中自由自在,美是生命代谢的载体,不是有滋有味的微量元素。因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只有在咀嚼苦涩的间隙体味一丝甜蜜。我想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努力调节已经老化的晶状体,体验成像在视网膜上的一团生气或戾气,面对生死之门时,向死而生而已。
在画廊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艺术思潮的延伸等方面,我还是比较赞同谌老师的观点。在回应大刘批判国内画廊运营理念唯资本市场马首是瞻的言论时,他贴出了自己的一篇文章。“画廊确实应该尊重艺术家的表达自由。但是,作为经济利益的中介,画廊必须建立自己的度量衡。因为,排除文化制度、社会思潮的制约,建立艺术作品的选择权是不现实的。画廊的经营,不仅要注重产生艺术的文化环境,还要揣摩金融资本的‘审美’惯性,不加甄别的呈现、推送政治诉求、道德评价针锋相对的艺术品,无疑会造成价值观对立。”很般配他带上了木框眼镜的新形象。“社会要求艺术品的创造者――艺术家,在文化的舞台上只充当配角,只负责本色出演,演绎的套路由一次次翻转的剧情承担。在这出曾经呈现和正在呈现的怪诞喜剧里,那个无处不在的‘戈多’才是主角――那个艺术试图解析不能明晰的,个体与社会共生的意识形态。”剃光了头两侧的头发,想法也更透彻了。我给他了个:给力。因此我以为,画廊业兴起很像工业文明前的地理大发现:发掘新大陆给旧大陆的股东奉上贵重金属和稀缺农作物,招来远亲的眼红近邻的嫉妒,此起彼伏的分赃与打劫等于本金的涨停与旁落。一个个哥伦布在未完备数学工具和航海仪器的情况下冒险玩命,理由是成为季风、信风、盛行风后的水手,一副高瞻远瞩乘风破浪的驾式,与画廊经理挺像。
天已经大亮,太阳还没出来。买了三个人的早饭,因为还有一个在家呆了半年的大一学生要早起上网课。“对呀,小朋友是视频的VIP,找个空儿,谍战片就能接上了。”付款成功的手机同时蹦出几个通知。微信里,贾校给孙子过百日的请柬、一张全家福、一张懵懂于幸福中的胖娃娃脸。原定在三月初吃的合欢面合并成一碗长远面,新娘不用配重,新爸有了负重,孩子已经抓取了家族的兴盛。拐进小区的侧门,前一天和我相撞、骑送餐车的胖小伙打来了电话。昨天问了,知道他是软组织挫伤,行动不便,说好今天一早去看他。我说是我为了上网约车突然走回头路的错,他说是他只想快没减速的错,以各自的瘀伤和后怕为代价,事故成了故事。
2022年7月10日 牛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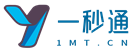 BITGET交易所官网
BITGET交易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