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自1975年从秦城出来的廿多年间,我的生活可以归 纳为争取平反、坚持为恢复党籍党龄不断地申诉和实事求是地为友作证。其间,我的海外亲友络绎回归,故友重逢;儿孙茁壮成长,真可谓桑榆晚晴好。
新时代的青年读者,恐怕很难理解当年涉及潘汉年冤案的“被审查者”,要想平反归队是多么困难。“四人帮”横行时,许多被颠倒的事情都不可能正本清源,何况潘案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性。如果没有邓小平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我们这些被扣上“反革命”、“叛徒”帽子的人怎能重新获得社会的尊敬和承认。使我欣慰的是我的儿女们还能理解我,给了我一个温暖的精神家园,并支持我不屈不挠地为平反申诉。
1975年5月中旬,
我被安排到大冶长女允中工作的地质队暂住。那时,大外孙女红星(弘莘)已十周岁,在地质队自办的小学读书,聪明活泼,十分可爱;小外孙女彤彤才三岁,比较娇气,爱哭。地质队职工的生活很艰苦,烧的是煤球炉,住的是平房。房屋的质量很差,每逢下雨,外面大下,室内就小下,家家户户要用脸盆脚盆承接漏雨。况且,三代人挤在一间小房里,夏热冬寒。允中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每周去县城一次,购买肉食蔬菜等副食品,来回要走三十里路。
允中说得好:此间情况,若与勘探开发大庆油田时相比,已是天堂了,那时睡在蒙古包式的帐篷里,两个人都穿着皮衣服,背靠背睡,还冻得发抖呢!她是志皋和祖母在世时最钟爱的孩子,却未被宠坏而意志坚强,她那能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以及为我添制丝棉衣裤等生活上的体贴伺奉,使我倍觉宽慰,真所谓精神胜物质也。
未几日,已调到福建地质队工作的大女婿尹志霖回来度探亲假,一家三代五口人,都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天气又热,自然极不方便。我睡在一张小竹床上。吃饭是在门外用木架支起一块木板,权当餐桌。不久,在新疆的小儿子文中和李心夫妇闻我已获释出狱,双双请假赶来探亲。地质队的党支部书记动员比邻一户人家暂迁别处,给我们增添一间住房。于是大家动手七手八脚,用旧报纸糊墙糊窗户,匆匆忙忙地将房间收拾干净,凑凑合合地就把文中夫妇安置下来住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庆团圆。
大冶民政局给我送来一张伤残荣誉军人卡,每月发给二十元生活费,这措施倒也符合我那时的身份。文中夫妇知我情况后,亦均认为继续上诉是必要的。李心也是上海支边青年,父母均健在,下面还有两弟一妹。李心支边后,其弟妹得以留沪,故李心甚得其父母钟爱,时常从上海给她寄罐头等营养品。文中患病时,蒙李心殷勤照顾,患难中生真情,终于结为伴侣。文中因过度劳累致病,被照顾,调到职工学校任教,不仅免去重体力劳动,亦获机会勤奋自修,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同时,未荒废高中的功课学业,为日后外出进修,打下稳固基础。文中夫妇在大冶只住了几天,就又去上海探亲。
大冶的文化生活很枯燥,难得有一次电影看。晚上在露天广场上放映电影,全队职工家属,以及附近农村的老乡们,均像过节一般,扶老携幼地去赶热闹。一次,电影队来 了,允中因白天工作劳累,不想去看,遂托邻居照顾我们老少三人去看电影。从住地到放电影的广场要摸黑走一段路,小彤彤走着一不小心,跌下了田埂,幸亏热心的邻居将她拉上 来、并护送我们回家。如今回想起那时的生活情景,倒也挺有意思的。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央最高的几位领导人恩来 同志、朱老总和毛主席竟在同一年间相继逝世。我从广播中惊闻受到全国军民一致衷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立即泪如泉涌,血压猛升,因悲恸过度而晕倒。经地质队医生抢救苏醒后,不禁痛哭出声。但不久却传来上面不准召开群众大会悼念周总理的规定,大家都无法理解和接受。虽然在乡下,离首都太远,信息闭塞,难以了解“四人帮”乘机作乱篡权的阴谋,但我们仍悄悄地通过各种不同的追悼活动,寄托心中的哀思。文中从新疆来函安慰我,并告以他们四十二团团部为敬爱的周总理召开追悼会时,他被推为恭读祭文的代表,全体官兵均不顾上面禁令,肃静默哀。
那年噩耗频传,同年夏天,朱总司令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举国悲痛,我用五言格式写了长篇悼词。又见报端公告,中央正公开征集散落在外的毛主席手迹墨宝。我就写信寄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求中央将当年毛主席亲笔饧购线装古籍书的一纸清单,复印一份给我们风雨书屋同人,留作永久纪念。
虽然中央对此没有复示,我亦未再去信催问,但后来听说,阿英病中,中央办公厅冯文彬同志去慰问时,曾询及此事。阿英告诉他:“确有此事,我们完成任务后,将此清单交与黄慕兰即定慧同志保存的。”我确切地记得,毛主席亲笔书写的这份买书清单、恩来同志1938年的亲笔表扬信以及刘少文带来的聂荣臻同志嘱北上共商大计的亲笔信这三件珍贵文书,是我亲自珍藏于上海通易公司的保管箱内。1955年我受审查时,由公安部会同人民银行破箱取证,均已收归内部存档保存,故我坚信定在内部妥为保存不致流失的。
大冶属黄石市,我的第二次申诉,是我带了外孙女红星,从大冶乘火车,亲自送到黄石市委组织部,请他们代为上送的。那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是赵辛初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宛希俨烈士元配夫人的堂兄弟,但昌杰儿亦从未见过这位堂舅舅。因此,我想他是一定会将我的申诉代为转送给中央的。
因为我的到来,似使允中夫妇家庭失和,我心不安。大中来接我去沙市暂住。她的丈夫曾抗生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过去在北京曾与我见过面。毕业分配后,两人本不在一地工作,承领导照顾,将他俩一起调来沙市,免去牛郎织女分居之苦。他俩相互支持,共同创业,均学有专长,令我欣慰。
此时他们已育一男,名曾群,比红星小,比彤彤大,亦聪明活泼可爱。沙市系小城市,生活方面比在大冶乡下略优些,住房虽有自来水,但无卫生设备,家中挑煤饼、倒便桶等重劳动活,均由抗生承担,劳而无怨,夫妇俩感情甚好。
1976年4月,我与一中同返上海。一中已与何士钦结婚,家中只有一间房,前面有大阳台是其婆母住的。因婆媳不和,一中意将我的临时户口转到原先带过文中儿的保姆丁彩英家借住,丁欣然接纳。彩英家住茂名路,已婚,抚一女,安顿我住前面以玻璃窗封住的阳台上,床边有一书桌。丁家地近复兴公园,清晨我就步行去公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人民 欢欣鼓舞,我也预感到自己的冤情将有出头之日了。两年多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在上海又第三次上书进行申诉,那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是彭冲同志。
1978年冬,我从上海回到北京,进行第四次上诉。当时文中、一中已获准赴美留学,杰儿、平儿均为他们送行。我们在京合影留念,平儿还写了一首七绝,为文中他们祝贺勉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条战线均在拨乱反正, 平反冤假错案的历史巨潮更是势不可当,我日夜期待的平反佳音也真的传来了。1980年4月上旬,邓颖超同志派秘书赵炜来杰儿家通知:第二天派车来接我去中南海谈话。当时邓颖超同志已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党内同志们对她亲切崇敬地称为邓大姐。次日,我带上志皋在美国与文中、一中见面后给我写来的感谢信,以备询问。到中南海邓大姐办公室,因公务繁忙,邓大姐嘱秘书杨荫东代为接 待。杨态度恭谨,站在楼下迎接。果不出我所料,杨首先询问上海通易信托公司海内外现尚健存的董监事情况,我将志皋来信呈上(邓大姐审阅后,由中央收存归档了)。随后杨又询问了我一些其他情况,均如实奉告。
三天后,邓大姐令秘书到杰儿家来传达慰问之意,送来她从自己工资收入中拿出的两百元,嘱杰儿为我买软卧火车票送我回沪,并指示:沪先解决户口、工作、公费医疗待遇等问题,最后再解决住房和恢复党籍党龄问题。杰儿全家和外孙女红星均在场,听得此喜讯,举室欢腾,为我祝贺。
杨又传达嘱我再写一份有关发现向忠发叛变前后经过的 材料,因此事党内长期未公开过,而我是最早发现报告党组织的当事人,理应补述当时情况留存中央存档的。我随即遵嘱写好材料送上去了。此次虽因公务繁忙,未能获邓大姐接见,但我已感同身受,誓当仍尽力之所及,再努力为党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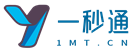 BITGET交易所官网
BITGET交易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