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征程已经开始了。站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间点上,我们清晰地看到,国际市场已成中国市场的延伸,而中国市场更已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后,中国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快速接通全球资本血脉,以前所未有的高光吸引着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但需要理解的是:中国为什么需要如此迅速地开放金融、资本市场?
全球科技资本争夺战空前激烈
毋庸置疑,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是伴随发达国家一般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这个时期,中国可以依托“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人富有智慧而勤奋创造”实现经济的快速进步。但4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能转移的都转移了,不能转移也是他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保持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站在这个角度看,或许大家不能简单理解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而更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到一个新境界,一个必须直接使用人类最前沿最核心的技术,并借此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这样的技术从来都是原创国或企业必须严格限制外流的领域。
正因如此,中国已经无法依托外商直接投资(FDI)去获取核心技术。这决定了中国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自主创新,突破基础科学瓶颈,研发原创技术,并以此形成中国经济未来的“核心技术集群”。
原创?谈何容易。
历史地看,任何一次人类经济的科技质变,必须伴随“科技资本”的巨额“挥霍”,工业革命如此,信息革命更是如此,而未来世界所期许的“智能革命”呢?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工业、信息、智能”看作三次经济革命,那它们所对应的“科技资本需求量”一代胜过一代,并呈“指数级”增长。只有获得足够的科技资本、股权资本去支撑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国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中国必须更大程度上开放资本市场,为吸收全球股权资本、科技资本创造必要条件。同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改革、完善、强化国内大市场,构建对全球“科技资本”的吸引力。这是当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现实是,全球“科技资本”争夺早已白热化。这实际体现为: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无一不采取极端手段全力推高股票市场,构建极度活跃的股权资本市场;与此同时,科技企业股票市盈率之高远超传统想象力,以此支持其“战略性关键企业”获取足够的科技资本——股权资本;采用难以置信的“科技战”手段,最大限度地打压其他国家的科技能力,包括以各种金融手段争夺科技资本。
如何理解“极致性货币政策”?
如果大家能够认清全球科技资本的稀缺性,能够看清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科技资本的争夺已经白热化,是不是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发达国家长期“大水漫灌”的政策意图?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对本国股权资本市场的呵护力度前所未有,而在全球经济均受“八大现实制约”的条件下,他们不惜采用“基础货币资本化”方式全力营造股市积极向上的金融环境。但这是否会带来股市泡沫、恶性通胀的后果?实际上,基于“八大现实制约”条件,第一,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第二,总需求严重不足迫使传统消费物价长期处于通缩状态。这明显为发达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功能、确立更加适宜科技资本扩张的货币政策诉求”提供了绝佳的基础条件。

理论上说,以伯南克、耶伦、鲍威尔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主流学派,他们以更加务实的姿态大胆地提出:在全社会债务率过高的情况下,唯有大规模向金融市场释放长期、超长期的基础货币,让基础货币充当国家资本,才可能大幅提高金融市场的资本生成能力,才可能在避免经济滑落的同时,有效降低债务率。同时,这样的政策手段必然会大幅推高股市,从而为充分集聚全球科技资本提供坚实基础。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今条件下“滥发货币”真会导致通胀?其实,“八大制约”已经极其严酷地弱化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总需求,当货币投放无法转化为消费需求之时,当货币投放无法转化为传统产业的原材料需求之时,那货币投放又如何推高消费品价格?
站在这样的角度认知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实施“长期基础货币+长期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效果或许不能再用简单的传统指标——比如通胀率加以考量,而更为突出的政策意图在于,尽最大可能弱化对短期经济指标的关注,争取最大程度“独霸全球科技资本”,为本国赢得更加坚实而长远的经济未来。
其实,发达国家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察的指标可能已经改变:第一,已经转为观察“一段时期通胀均值”,以此加大货币政策对短期物价上涨的容忍度;第二,置入“就业率”观察指标,以此观察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本扩张能力。换言之,货币政策必须特别关注“企业股权资本的融资能力和对未来的投资能力”。同时,更要观察与“国际资本争夺战”相关的一系列指标。
跨国资本之水的治理之道
短短两年时间,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股市、债市。同时,大家可以看到:陆港、港陆(北上或南下)的资金越来越明显而清晰地刻画着中国金融市场的波澜印迹。但可以肯定,这仅仅是开始,更大的双向流动、更猛的波澜起伏还在后面,会把中国金融市场导入新纪元,并为之注入新能量、新特性,但更需要中国重视的问题是:全球金融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必然会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量级更大、前所未有的金融冲击和巨大风险。
发展中国家如能够管好、用好国际金融资本,那将是福,但如果管不好、用不好,那则是祸。非常不幸,从人类百年发展历程看,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甚至包括日本、韩国都曾因为资本开放,跨国资本大进大出而陷入“金融危机”。或许正如中国那句老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1997年,亚洲当年的“四小龙”、“四小虎”之所以陷入金融危机,其关键表象都是一个:外汇储备不够支付到期外债。而之所以陷入外债危机,关键在于他们试图以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吸引外资,以此对冲其贸易项下的巨额逆差,从而获得收支平衡、推升经济增长。但是,外资进入后并未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而是投机套利,结果导致这些国家或地区实业成本不断提高,经济空心化、泡沫化。在此背景下,固定汇率制导致本币该贬不贬、严重高估,给了国际金融大鳄货币狙击的可乘之机。
现在,中国已经站到“加快开放金融”的历史当口。此时此刻,必须汲取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教训:第一,以长期政策支持“长期投资偏好的优质资本”投资中国的同时,必须充分抑制外资短炒、爆炒股市和楼市的行为;第二,既要大量有效使用优质国际资本,同时也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以市场手段引导中国民众长期而从容地进行股权投资,并将中国资本的定价权牢牢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第三,改革货币政策手段,坚决防止营造只适于金融套利的货币政策环境,切忌引导巨额短期债务资本流向中国空转套利。历史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几乎都是因为外汇流动性短期枯竭所致。这说明,巨额短期外债是引发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关键诱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坚持对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实施严格的“通道管理”,绝不能容忍金融自由化之下的“无序自由流动”。历史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诱导下任由资本无序跨境流动,当金融危机突然爆发之时,政府甚至不知自己的国家到底背负了多少外债,也不知该向国际社会借入多少外汇才能应付市场支付需求。
毫无疑问,在全球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调整、疫情蔓延的背景下,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必然带来较大挑战,这无疑会向金融管理提出新的要求。现在有些非常危险的认知:其一,境外资本占比小就不会导致过大的风险;其二,必要之时,可以“关门打狗”。
历史证明,金融大鳄攻击一个经济体,往往只需一笔“启动资金”,犹如导火索最终引爆炸药包一样,导致金融危机的终极力量往往是“羊群效应”。另外,一个国家关闭资本账户,要付出巨大的国际信用代价。历史证明,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尤其是“中产负债人群”,或将一贫如洗。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借助全球科技资本去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去创造足以支撑未来长远发展的新财富,并以此有效覆盖和化解债务风险。随着中国经济“十四五”规划正式实施,新发展格局战略定盘,这个过程已经拉开帷幕。但正如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指出的那样: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3、4期)

2021年第3、4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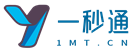 BITGET交易所官网
BITGET交易所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