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昆仑资管中心 张玮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周二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未来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考虑金融周期;货币政策应该抑制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并具有保持金融稳定的公信力;央行既需要影响短期利率,也需要影响长期利率;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国际协调。

我们认为,孙国峰所长此次讲话,意在表明货币政策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保增长过渡到防风险。在此背景下,长端利率不大可能维持低位,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关系也将显著。我们认为,把握孙国峰所长的讲话精神,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货币政策框架的三个阶段
截止到目前,全球货币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各国货币政策施行的是“多目标、多工具”;80年代以后,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过渡到“单一目标、单一工具”。在此期间,以通胀为代表的物价稳定是主要目标,一般目标为“2%”,单一工具多是针对短期利率的调节。相比之前的“多目标、多工具”,第二代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积累了大量风险:紧盯住2%的通胀目标会使货币环境长期宽松,以致引发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出现资产价格泡沫。长期积累会引发金融危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货币政策正在向“第三阶段框架”转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更加重视金融稳定,结合金融周期,将风险防范作为重点。
二、由“事前忽视,事后补救”到“预期管理”
前面提到,第二代货币政策以经济增长为基本出发点,对金融危机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危机处理问题上多是“事前忽视,事后补救”。结果往往导致金融层叠、产品嵌套,负债端急剧膨胀。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处理相对困难。而第三代货币政策强调“预期管理”,这里又包含以下两点:
一是破陈出新地提出要与金融周期将结合,经济与金融不可割裂,忽视金融周期的货币政策,往往会酝酿较大的金融风险。对此,货币政策抛开了“中性”的矜持,开始关注金融稳定和资产价格,强调去杠杆和防风险。众所周知,在金融周期的各个阶段,资产端和负债端有个此消彼长的比例关系。负债过度意味着整个“社会信用”超出实体承受能力地膨胀,各部门杠杆高企,危险程度自然不可小觑。举个例子,从四部门模型观察:非金融企业部门扩大生产的意愿本就强烈,该部门多年来杠杆率一直处于高位,尤其以早年间过剩产能的重工业国企最为显著;随着金融深化和广化的不断推进,金融部门杠杆率也不断增长。自2015年开始,政策层有意将杠杆导向居民部门,以此化解其它各部门的杠杆风险,居民中长期贷款也在那段时间整张的最为剧烈。但居民部门毕竟承载有限,如果再不闻不问,最后杠杆一定又会落在政府部门头上。所以,“金融部门降杠杆,实体部门去杠杆”成了近年来政策层反复提起的口号,并且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作的核心。负债端与资产端要保持合适的比例,脱离金融周期考量的负债过度膨胀,只会让风险不断积累,“滚雪球”式增长。
二是充分认识到不应营造长端利率低位的预期。以往的观点认为短期利率的重要性仅仅来源于它们对长期利率的影响,即长期利率是未来短期利率的风险调整期望值。但最新的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增加了家庭和其他经济主体向银行提供的资金,可能增加贷款的风险转嫁效应,其原因在于银行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尤其是那些资本金较低、未能将贷款违约风险完全内部化的银行。如果商业银行预期中央银行会在金融市场承压时降低利率,它们会大举借债或发放更多高风险、低流动性的贷款,从而增加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此时,中央银行最好通过改变货币政策来改变银行的冒险动机,更不应当营造实际利率将长期处于低位的预期,以免银行的风险行为倒逼央行继续维持低利率。因此,央行需要在经济复苏态势明确后有序提高政策利率,以抑制加杠杆行为和资产泡沫,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走向复苏,各国央行都有意迎来货币政策拐点。美国方面,渐进加息和缩表正稳步推进:2014年,美国率先推出量化宽松,2016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同比增速保持了五个季度的反弹,就业市场也持续修复,劳动参与率停止下降,失业率降至4.1%的低位。今年美联储加息节奏也较过去两年明显加快,同时10月开始缩表。加拿大方面,今年7月也实行了七年以来的首次加息,9月又再度将基准利率上调到1%。英国方面,更是在今年11月将利率提高到0.5%,为十年来首次。不仅是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也屡有“加息”报出:2017年以来,墨西哥累计上调基准利率125个BP,亚洲的韩国也在今年11月30日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BP。可以预见,为了防止资产价格过度上涨,将会有更多央行步入“加息”行列。
三、操作更具针对性
从货币政策角度抑制金融风险,操作层面最重要的就是由数量型变成价格型。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着眼点在于总量控制,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政策调控存在“放大”和“时滞”效应,而且波及较广,不易控制;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将各个市场利率分开操作,更有针对性。
金融加速器理论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假设提出的,其两大核心概念是“外源融资溢价”和“净值”。银行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企业从信贷市场获取资金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即外源融资溢价,而这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系统之间最主要的施力媒介。在此基础上,由于流动性的不对称性和资产价值的不对称性,实体经济摩擦或金融摩擦会导致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引起净值的波动,且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信贷渠道(溢价)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净值)对信贷周期施加逆向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银行与企业间直接的信贷渠道,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能使银行减少贷款供给,从而增加了那些依赖于银行信贷的借款人的资金成本;二是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渠道,提高短期利率会降低银行净值,并减少融资的流动性,从而对银行贷款产生负面影响,引起银行贷款总量的显著波动。同时,货币政策紧缩也加剧了小企业在库存和投资决策中的流动性约束,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削弱了小企业的信誉度,进而减弱它们筹集任何外部资金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银行贷款。
正是由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存在,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操作层面才被打上了“粗放”的标签:针对货币量的调控往往没能将实体和金融两个层面隔开,在经济衰退期时期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政策往往最终铸就了金融泡沫的新高度。而且,不仅是实际效果不可控,再传导时间上往往还存在“时滞”。这就意味着一旦短时间内没见到效果而采取了频繁的货币操作,往往会在之后的某个时间“矫枉过正”。所以,今后的货币政策,或会发挥“价格型”优势,将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分隔开,对金融市场不同层面和交易品种的产品价格更有针对性的引导,并配合资管细则“联合出击”,引导金融和实体的良性发展。
四、传导机制方面更加重视银行的核心地位
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间接金融为主,以直接金融为辅,商业银行在经济金融中的低位至关重要,既是借贷增加,经济增长的主推力量,又是信用膨胀,杠杆高企的核心根源。孙国峰提到:银行是一类特殊的机构,其背后有政府显性或隐性担保,所以天然具有冒险倾向。如果中央银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水平,就会鼓励商业银行的冒险行为,商业银行有可能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形成博弈。所以,无论是处于一直风险考虑,还是金融监管层面,都会更加重视商业银行在货币传导中的核心地位。商业银行自然也就成为“金融降杠杆”背景下,监管督导的重点。从近期出台的监管政策看,无论是同业、理财、非标,最终落脚点都验证了这一观点。
五、注重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问题
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的高企,货币政策外溢性越发明显。从政策实践看,近期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协调明显增强,主要货币当局普遍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新兴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增强汇率灵活性,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从“不可能三角形”判断,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项目开放不能三者同时满足。今年以来,不断有官员表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不会倒退”。综合考虑美欧等发达国家与我国利率中枢的差异,我国政策当局势必会牺牲一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以保障汇率稳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汇率稳定并非固定汇率,而是被限制在一定的波动区间,政策层对汇率的波动频率有更大的接受程度。在此设想下,货币政策与汇率的协调程度将有所增加,料想2018年汇率波动会更加频繁,呈现出与利率中枢更高的相关性。
总结
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而是更要保障金融、经济运行平稳。货币政策更“细微”。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会减弱,将逐步增强与汇率的联动性。展望未来,在经济复苏态势明确后央行应该有序提高政策利率,以抑制加杠杆行为和资产泡沫,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债市需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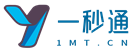 BITGET交易所官网
BITGET交易所官网